

? 对话人:
葛兆光
著名历史学家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前院长及特聘资深教授
多所国内大学兼职教授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多所国外大学客座教授
易中天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高等研究院院长
时间:2023年4月3日 下午地点:厦门大学科艺中心“海岳学术云”系列讲座
葛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实际上是价值观和方法论。我觉得作为一个学生,在大学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听讲座。
一个好的大学教授,他出来做讲座,一定是把他研究里浓缩的精华拿出来。虽然你可能听不懂他的专业,但是你可以学习他的思维方式,这个比我们听到的具体内容还要重要。
而且大学不是读出来的,大学是熏出来的。为什么要考好大学,要考比方说像我们厦门大学这样的百年老校,它有一个文脉在这个地方,这个文脉是代代传承的,然后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讲座来形成一种风,这个风就把我们熏出来了。
非常感谢葛兆光先生今天的精彩演讲,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价值观和方法论的问题,那么我就照例问三个问题。
- 第一问 -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易中天我常常会被媒体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而这个问题我是答不出来的,我在厦门大学工作的时候,最早是在艺术学院当艺术研究所所长,后来调到中文系教美学。
我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进入了历史学界,所以想请葛先生回答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葛兆光关于为什么要学历史这个问题,是千百次问历史学者,而历史学者最反感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一直在努力试图给出正面的回答,但是这个正面回答首先是一个反面的问题——假定没有历史会怎么样?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看过一个,这个讲的是世界上如果没有人类,五天、十天以后会怎么样?一百天以后会怎么样?最后五年以后会怎么样?一百年以后会怎么样?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撼。
于是我按照这个同样的方式来思考,如果没有了历史会怎么样?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法寻找我们自己,我们姓什么、我们从哪儿来都不知道。这是从反面来说“如果没有历史会怎么样”,大家能够想象到,就像“没有人类世界会怎么样”一样,它的灾难性后果是什么,大概能够从反面去了解。
但是从正面来说,我们人都会生病,这个社会、也会生病,历史学者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给你诊断这个病源的,让你知道你有什么病,是怎样得的病,或者说你这个病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但历史学者绝对不是开刀动手术、开处方的医生,后半截应该交给政治家来解决。我们历史学家有责任去诊断病源,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问题,它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
- 第二问 -
如果做不到最好的历史研究怎么办呢?
易中天葛先生今天讲什么是好的历史研究,我觉得不仅仅是做历史研究,做别的研究也应该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做传播研究,那我们就要讲什么是好的传播学研究,还有什么才是好的生物学研究、什么才是好的文艺学研究……不管哪个专业都应该设定这么一个标准。
古人说“取法乎上者,仅得乎中”,如果我们连这个最好的标准都没有,我们就做得一塌糊涂。但是,如果做不到最好怎么办呢?
葛兆光努力做到最好。因为做历史研究,我们做不到100%的还原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努力去逼近真实,这是我们现代历史学的一个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去逼近历史,但是千万不要断言我们绝对能够恢复历史。那么同样,当我们做不到最好,我们努力去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 第三问 -
如何写一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易中天我非常赞成葛先生刚才提出的要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我们高等院校的一些分科很奇怪,比如哲学分为哲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但黑格尔早就说过,哲学就是哲学史,或者说哲学史就是哲学,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分开。
所以我很赞成“我们的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我们的中国史是没有世界的中国史”这种批评。但是话是这么说,当真做起来很难,因此我也有很多实践当中的困惑。
我们碰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有条件做这件事。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不关心世界,世界也不关心中国。现在中国强大了,大家都开始关心中国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也必须关心世界。在这个前提下,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有可能写出来的,但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之难。
葛先生写过一本关于禅宗的书。曾经有一个美国学者叫布洛克,他到中国来访问,他就问我什么是禅宗?我讲了大概一个小时,因为禅宗不是讲不立文字嘛,我就跟他讲了半天,他说我明白了,我们美国人弹钢琴弹得好的也不看乐谱,他根本听不懂。
我很想问的问题是,当我们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而且当我们写一部历史,不管它是叫做有世界的中国史,还是有中国的世界史,它总得有个什么线索。
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倒过来中国中心论。那我们到底是多中心还是无中心呢?还是用一个超越了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的更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做这个事呢?我很想听听葛先生意见。
葛兆光易先生讲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中国人写中国史或者写全球史,到底应该有没有我们的立场,有了我们的立场以后,会不会导致一种中国中心主义,这都是我们学界现在特别关心的大问题。
刚好前三年我们做了一个音频节目,叫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我就在里面讲了一段我们的立场。
,要强调所有的民族、、文化和历史都应该是平等的。
第二,我们得谦卑地承认,历史学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是可以360度无死角地观看历史的人。我们不得不有我们的角度,所以我们只能从中国出发。
第三,我们从中国出发,不是强调中国的价值、中国的立场,而是说我们中国的角度、我们中国的眼光。
比如郑和下西洋,即使我们从中国出发,我们仍然认为郑和下西洋并没有真正地带动全球化,没有使得全球商品贸易连成一体,促进世界的改变,而大航海时代的欧洲、葡萄牙、西班牙的全球航行和它的全球贸易才真正促进了全球化。
这样就不是中国的立场,或者仅仅是用中国的角度,或者出于中国的自尊、或自信、或自卑来评价历史,而只是从中国这个角度看过去。
而且我们特别强调一点,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是跟从美国出发的全球史、日本出发的全球史、韩国出发的全球史,印度尼西亚出发的全球史互相配合,然后互相构成一个全景的全球史。
因此我们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你千万不要带有过度的自尊、自负或者是自我放大,我们跟别人的眼光和叙述是可以互补的。
我们现在并不是没有办法来克服,而是说当我们克服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面临一些已经习惯了用自尊自大的视角来看历史的人的质疑。我们会非常尴尬地发现,我们的这个历史观在大众里还没有完全改变,所以会面临很多困难。
易中天谢谢葛先生,现在把提问的机会留给同学们。
 同学1
同学1
葛教授好,我是文学系的学生,我们在美国文学课上会学美国史,就是Peter Watson的Ideas: A History of Thought and Invention。我想问一下葛教授,以这种思想作为一个主线,然后进行历史的编纂,它是不是也会成为我们未来研究历史或者是任何人文社科的一种主流趋势?因为他那本书把中方和西方思想(ideas)之间的交换说得非常好。
葛兆光我同意这种做法,我给你推荐一本我最近看的书。我认为这本书把东西方连在一起,把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知识和文化传播写得非常好。
这本书就是法国学者格鲁金斯基的《世界的四个部分》,他讲的是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创了早期的全球化,它把各个地方的知识、财富和文化都交融在一起。
这本书的写法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比如作者把墨西哥城、印度果阿、菲律宾马尼拉、中国澳门、中国广州、中国泉州,甚至巴达维亚这些不同的地方都连在一起,告诉我们它们互相之间怎样刺激、促进、变化,这个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历史学界过去有一个缺点,就是讲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时候,只是在写谈恋爱,但是没有写谈恋爱以后生的孩子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推崇格鲁金斯基的这本书,格鲁金斯基被认为是布罗代尔之后最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我觉得这本书值得向大家推荐,做世界史的人也可以学习他的这种写法。
 同学2
同学2
老师你好,我刚刚看到你有说“新论述、新观点、新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对错而在于接下来有意识跟进的部分,要看到争议的价值和思考的价值,不要做死水,要做水花。”
我以后想就读于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也会从事一些历史研究相关的内容,所以我想问一下,对于我们这样的新时代青年,怎样去做一个水花?怎样去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葛兆光我只能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跟你讲一下,读书、写作和研究怎样能够避免平庸。我们看任何文献和历史资料的时候,都要先问它是不是真的对,总是带有一种怀疑的眼光。
这就是胡适当年说的,首先你要有怀疑,不然你就提不出问题来。所谓小水花,如果你是没有问题的,你连水花都不是,你就是水里面的一份子,但是你要是提了个疑问,你就是那个水花,如果这个疑问在无数的证据下证明它是成立的,那这个水花就大了,说明你已经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就像季羡林先生写《蔗糖史》,他其实就是一个疑问——为什么敦煌文书里面有一个汉字写的叫“煞割令”?以前甜的东西都用“煞割令”来描述,那么“煞割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他马上就追溯,用积累的知识来判断它跟梵文、巴利文的“糖”有关系,但是他同时又联想开去,英文、法文、德文的“糖”为什么都跟这个音很像呢?那问题就出来了。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它必须有更广博的知识和更多的语言能力,然后你才能把你的小水花、你提的疑问变成一个大的问题,然后才去做细致的研究。
胡适讲得很对,你如果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你随时随地提出疑问,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但胡适也讲:“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疑问与证据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能够让大家注意的小水花。
易中天那么疑问怎么产生呢?
葛兆光禅宗有一句话叫“死于句下”,他骂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这个人死于句下”,你就等于把这个话全部接受了。所以你在听任何话、读任何书的时候,要保持平等对话和质疑的立场。你不能说你讲的都是对的,我就学习。
为什么我们经常强调大学生与研究生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大学生是接受常识,而研究生是挑战常识。到了研究生阶段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任何东西你都要先问几个为什么。“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就是胡适一再教给我们的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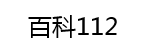 玩家必看教程“新友娱乐真能买到挂吗”(确实是有挂)_抖音推荐" data-original="http://www.shanghaiguisu.com/css/1.jpg" />
玩家必看教程“新友娱乐真能买到挂吗”(确实是有挂)_抖音推荐" data-original="http://www.shanghaiguisu.com/css/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