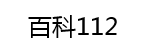夜色正浓,惨淡的月光透过窗帘的间隙洒落在卧室里,犹如披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惨白外衣,原本普通的房间,此刻竟显得有些森冷与诡异。
一名年轻的男子正陷入熟睡当中,胸膛随着呼吸,轻轻起伏着。
偶尔有风吹过,卷起窗帘的一角,月光照在男子的脸上,棱角分明,细腻的绒毛清晰可见,只是他的五官微微皱起,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他似乎正陷入异常恐怖的噩梦当中,浓眉深锁,原本平稳的呼吸陡然间变得急促起来,眼珠在紧闭的眼皮下急促地打转,额头上的青筋根根暴起,双手更是无意识地攥紧被子,用力之深,以致连手指关节处都泛着青白。
而他俊朗的脸庞更是变得惨白无比,散发着源自灵魂深处的无助与惊惧,好像整个人都陷入了如浓墨般黑暗的泥潭之中,越是挣扎就越陷越深。
终于,一阵剧烈的喘息过后,男子犹如从地狱中逃脱一般,眼睛“簌”地一下睁开,惊坐而起,大口喘着粗气,大滴大滴的汗珠也从额头上滑落。
他抬起头来,惊恐不安得扫过房间里的每个角落,似乎是还没从噩梦中醒来,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回到了人间,还是仍然身处在梦境中。
不知过了多久,房间里熟悉的一切,总算让他惊慌的眼神恢复了几许神采,他松开紧攥着的被子,才发觉冷汗早已经泅湿了衣衫,浑身上下被一股阴冷包围着。
艾天旗的心跳终于逐渐回归平稳,他活动了一下因极度紧张而略显僵硬的身体,扯过一件夹克外衣披上,双手支撑床沿,呆坐在那里。
然而身体并没有因为包裹在外套里而感到一丝温暖,这个真实到可怕的梦境仿佛要把自己拉入无底的深渊,,即便是此刻,梦境里那刺骨的阴寒仿佛仍未散去,一点点地蔓延过全身,浸入他健康的小麦色皮肤,渗透进他的骨髓,抽离不去。
有那么一瞬间,艾天旗甚至怀疑自己究竟是否还活着。
每一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的诡异梦境,犹如真实发生过一般,一幕幕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自己眼前。
这些情景,真的,只是一场噩梦吗?
天旗定了定神,起身来到桌前,扭亮台灯,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冰凉的水流从喉咙滑过,落入腹中,带来一股清凉,不经意间,目光落在平摊在桌面的一本笔记上,他顿时周身如坠冰窖,握着杯子的手就这么定格在半空中,难掩的悲伤涌上心头。
纸张早已泛黄,页角更是布满了细细的裂纹,犹如迟暮的老人,饱经岁月的风霜,早已变得脆弱,轻轻翻过一页,每一张纸上,都沉积着历史的沧桑。
这笔记本正是姨妈的遗物,它的存在毫不留情地提示着这个失神的男人,姨妈是真的不在了,就在这栋房子里,就在自己的眼前,姨妈神情诡异,身体扭曲地倒在地上,浑身都是……
想到这里,忽地口中泛起一阵难以形容的苦涩,艾天旗一扬手,将杯中的水大口咽下,不愿再面对这段此生都无法接受的回忆。
前几天的中午,艾天旗的影视作品入围了;为期三个月的纪录片大赛的总决赛,他兴高采烈地冲回家打算和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但在打开门的瞬间,他却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姨妈浑身古怪的肿胀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一根根黑紫色的血管怒张着,仿佛随时都会冲破皮肤的束缚迸射出来,黑血从身体各个地方渗出,一股浓烈的恶臭扑面而来。
她的眼珠子更是爆涨得仿佛都要从眼眶中挤出来似的,就这么直勾勾地对着天旗的视线,像是在诉说着她死前的绝望和痛苦。
如果不是尸体身上穿的那件衣服,天旗甚至没法认出这个胀得像被水泡过几天的尸体,就是从小朝夕相处、亲若生母的姨妈!
天旗缓缓倒退着,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拼命地摇头,试图把眼前的景象从自己脑海中驱赶出去。但当他的目光再度落在地面上时,姨妈无言的尸体,却依然安静地躺在那里。
这一刻,天旗的世界崩溃了,急怒攻心之下,他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姐姐艾天格正伏在床前泣不成声,柔软的长发遮盖住被泪水浸没的面容,极力压抑的呜咽声,如刀子般凌迟着艾天旗的心脏。天旗突然像疯子一样,从床上冲下来,几乎是扑到电话机前。
然而不等他按下个数字键,父亲却一声大吼,呵住了他,夺过话筒一把按下。
“爸!你干什么!”艾天旗猛然扭头,满眼的不解和愤怒,他想拿起电话,但一只苍老的手却死死按住了话筒,他怒视着父亲,两人的脸色满是阴鸷。
父亲阴着脸,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不能报警,绝对不能!”
即使是现在,艾天旗依然还能清晰地回忆起父亲那日的模样,长这么大,他头一次从父亲的脸上看到这样复杂的神情:暴怒、恐慌、哀伤、甚至是绝望……
他从来不知道一向强悍的父亲也会有这样绝望的一面,只是当时,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下,他根本没有心思留意到这些细节,反而如同发泄般冲着跟父亲一通怒吼,似乎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驱赶走心中的痛苦。
天旗无法理解父亲古怪的举动,姨妈是被人害死的,为什么不让自己报警?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姨妈死不瞑目?
自那天过后,父子俩就一直没有说过话。
天旗叹了口气,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父亲的房门口,他在门口踟蹰了片刻,最终,还是轻轻推开了门。
父亲没有察觉到他的到来,依然在熟睡当中。
因为姨妈莫名的遇害,他已经很多天没和父亲说过话了,但此时,看着熟睡中也紧皱着眉头,似乎满怀心事的父亲,天旗还是忍不住鼻子发酸,一抹泪水悄然模糊了视线。
从小视若生母的姨妈遇害,让自己一时乱了心神,可这又怎么能责怪父亲呢?或许是父亲知道了一些内情,不想让自己担心,才选择了藏在心里独自承受吧?
注视良久后,天旗一句轻轻的“爸,对不起”不自觉的脱口而出,说完他也有些不知所措,生怕父亲醒来,看见自己此时的不安和愧疚,于是连忙转身离开了父亲的房间。
就在他转身的瞬间,年老的父亲抿了抿干裂的嘴唇,一滴隐忍了许久的泪水,顺着父亲眼角的皱纹缓缓地滑落……
第二天早上,天旗从楼上下来,看到父亲正坐在餐桌前。
听到楼梯传来的响动,天格从厨房探出小半个身子,“天旗,早饭在桌上,你们先吃,我再煎个鸡蛋。”说完又闪身回去忙活。
拉开椅子坐下,天旗打量了一眼坐在对面的父亲,喉咙耸动了一阵,略有些尴尬和忐忑,但终于还是喊了一声:“爸。”
父亲依然板着脸,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淡淡的应了一句“吃吧”,只是那微微扬起的嘴角,彻底暴露了他的内心。
天格倚在厨房门口,手上端着盘子,却没有马上过去,她只是静静地看着餐桌旁的父子,脸上露出安心的神情。
从这一刻起,横亘在父子之间多日的块垒,便如同阳光下的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不见。
父子俩十分默契地没有提及姨妈遇害的事情,这是所有人都无法忘却的伤痛,或许,只能依靠时间来冲淡内心深处的痛楚。
姨妈的后事已经料理完,早饭后,请假多日的天旗回到了学校。
然而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些仿若真实的噩梦依然无时无刻不在纠缠着天旗,尤其是最近,甚至连父亲都出现在了天旗的梦境里。
又一次在大汗淋漓中惊醒,天旗面色惨白地坐在床上,回想着之前的梦境,隐约有一种不详的预感。
父亲被困在一个奇怪的瓮里,八根藤条从腹腔伸出,诡异的咯吱作响,似乎是一种狰狞的笑意,然后毫不留情的插入父亲的后心,贯穿了整个胸膛!肌肉被轻而易举地撕裂开,露出胸腔内尚在跳动的心脏,鲜血从伤口中喷涌而出,天旗甚至能感受到血液喷溅到脸上的温热感。
然而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父亲在无尽的痛苦中挣扎,想叫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就在他挣扎着想救父亲时,藤条上不知何时冒出无数的血色条虫!那些细小的虫子线儿似的源源不断的顺着藤条钻进父亲的身体里,很快,虫子再也挤不进父亲的身体,从毛孔中又涌了出来,父亲的眼睛已经爆涨得跟姨妈一样,大量的血水从眼眶里不断的溢出。
眼见着父亲的脸跟姨妈的死状慢慢的重合,艾天旗痛苦的嘶喊着,挣扎着,却无济于事。他竭力的想摆脱眼前的一切,可就在这时,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那个浑身都浸在血中男人嘶哑地喊叫着:“不要回去!不要回去!”
“砰!”的一声,整个人摔在坚硬的地板上,随之而来的是后背剧烈的疼痛,地面的寒凉刺激着艾天旗的神经,让他一点点的清醒过来。
衣衫一如往常被冷汗浸透,可这一次即便是已经从噩梦中惊醒,内心深处的恐惧却丝毫未减,身体的各处传来彻骨的疼痛,仿佛梦境里的藤条插进的不是父亲的胸口,而是自己!他用力地按着胸口,本想驱散心中的恐惧,梦里的场景却渐次清晰起来,仿佛自己身体的下方就是那个无底的黑洞,无法抗拒的引力牵引着他向下坠落……
再一次醒来时,电话正在耳边震动着,天旗拿起手机,电话刚好挂断,屏幕上显示着六个未接来电,都是姐姐打来的。
天旗心里突然“咯噔”一下,心头掠过一丝不详的预感,连忙拨回电话,电话接通了,却没有人说话,只是隐约听到姐姐的啜泣声。
“姐?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别哭,快告诉我啊!”天旗焦急地喊道,心中的不安迅速扩大。
过了片刻,电话那头却传来准姐夫振枫的声音:“天旗,赶紧来医院见你爸爸最后一面吧,你爸爸……你爸爸他出车祸了。”
手机从天旗手中滑落,重重地跌落在地上,隐隐的,还能听到振枫焦急的声音“天旗,你没事吧?天旗,你说话……”
然而天旗却对这一切毫无反应,他就这么保持着接听电话的姿势,呆立在原地,仿佛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失去了全部的知觉,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他甚至忘却了自己身处何地,是梦境,还是现实…天地间都失去了光亮,只有父亲满是鲜血的脸上,那扭曲的诡异表情在眼前不停地晃动……
天旗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从宿舍赶到医院的,也不记得是怎样揭起父亲身上的白布……接到振枫电话的那一刻,他就成了一具失魂的躯壳,内心满是难以言说的巨大的悲痛,仿佛置身在黑暗的深渊里不住地沉沦,绝望填满了身体的每一条角落,看不到一丝光明。接踵而至的打击让天旗次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身边发生的一切,他根本无力抗拒。
接连失去两位至亲,姐姐天格就是再坚强也扛不住了,瘫坐在那,将头埋在自己的胳膊里,在天旗没赶到医院的时候便已经哭的不省人事。
姐弟俩依偎在一起,彼此冰冷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却感受不到一丝温暖。
父亲的后事是在振枫的奔走下才得以顺利完成,料理完丧事,振枫瞧着行尸走肉般的姐弟俩心里也束手无策,出了这种事情,他也不知道要应该怎样去安慰。
“振枫,你先回去吧……”犹如木偶般呆愣的天格连说话都有些麻木。振枫也有些犹豫,他担心姐弟俩再出什么意外,但是考虑到姐弟俩骤逢巨变,多少需要时间来恢复,他也只能点了点头,轻握了一下天格的手“有事叫我。”
振枫离开后,家里顿时冷清了下来。
过了片刻,天格似乎是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来,从包里拿出一个古旧的本子递给天旗“这是爸留下的。”
“爸的遗物?”天旗情绪低落,接过本子时碰到了姐姐的手指,只感觉一阵冰凉,他心底微微叹息,拿着本子茫然地翻看着。
天格在一旁坐下,沉默了片刻,开口道:“我看爸走的时候没带他最心爱的紫砂壶,我怕他……走得不安心……”说着鼻子又是一酸,声音也哽咽起来。
天旗连忙搂过姐姐,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她。
好一会儿,天格才稍稍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她抬起头来,略有些嘶哑地说道:“这个是在爸的房间找到的。”
她说着拿过天旗手中的本子,,很快就翻到了其中的一页,她指着并将本子递过去给天旗看,目光也变得凝重起来:“你看,这些文字记载还有简笔画,我总觉得依稀有些印象,仿佛曾经在哪里见过……”
天旗凑在姐姐身边仔细地看着,越看越觉不对:“姐!爸怎么会有关于蛊的记录?”他说着不禁念了出来本子上的文字:“蛊中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无形虫灵……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取其独存者,便可为蛊害人。金蚕害人使人深重邪毒,胸腹搅痛,肿胀如瓮,流血而死……”
“胸腹搅痛,肿胀如瓮,流血而死……”他不自觉地又重复了一遍,忽然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天格 ,“姐,为什么这个描述和姨妈的死状一模一样?难道……难道姨妈是被爸害死的?”
“别瞎说!”天格赶紧捂住他的嘴,“你昏了头了,怎么可能是爸,他们可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至亲的亲人!”
“我也不想怀疑爸,可是你怎么解释爸不让我报警的古怪举动?姨妈可是让人害死的!”天旗一把按下姐姐的手,目光中的疑虑更盛,“更何况,在我们身上的谜团还少吗?”
“姐,你知道我们的妈是谁吗?姨妈也好,爸也好,他们说过自己的过去和来历吗?”他仿佛有些神经质了,紧紧拽着天格的手一字一句地说,“从记事起,我们的记忆里就只有这栋房子,小时候应该有的东西却一件也没有看见过……姐,我知道的你也怀疑过,别的孩子都有童年,都有爷爷奶奶,为什么我们没有?”
“尤其是你胳膊上的这道黑印,”艾天旗一把抓住天格的胳膊,将天格拽的生疼,逼着她直视那条黑色的印记,“姐你心里也清楚吧,没有胎记会长成这个样子。”
“够了!不要再说了!”天格打断了有些咄咄逼人的天旗,“无论曾经发生过什么,都已经过去了,他们一定希望我们好好生活。”说完,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房门走去。
天旗注视着姐姐的背影,冷冷地质问道:“是!是让我们好好生活,并且永远被噩梦缠绕着,是吗?!”
听到了“噩梦”这两个字,天格像被电击了一样,全身猛的震了一下,她的脚步停住了,回过头来,眼中充满着恐惧,让天旗好似看见了无数次从无尽噩梦中醒来的自己。
“你也不断的做噩梦吧,姐姐?”天旗从姐姐那藏不住谎言的清澈眼睛里,更加笃定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是双胞胎,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恐惧,那种感觉那么清晰,就跟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一样……你等着,我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