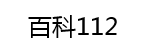鲍勃·迪伦的新书《答案在风中飘》(原作名:The Philosophy of Modern Song),很鲍勃·迪伦。
《答案在风中飘》书影
所选的66首歌里,多数是美国歌(除了The Who,The Clash和埃尔维斯·卡斯特洛)。他对“现代”的理解,和大多数人不一样。他没有选站在“现代”门槛(山巅)上的“披头士”,没有泰勒·斯威夫特和肯德里克·拉马尔,也不见那些受技术发展的影响或是影响了技术发展的音乐家。鲍勃·迪伦选来写的歌,像他近年发表的一系列翻唱专辑一样老派。老到有些歌你找来听,叮叮砰砰,哇啦哇啦,和今天即使相差不到一百年,听起来也古老得多。它们仿佛穿过电灯发明前的漫长黑夜而来。
布鲁斯、乡村老歌,当然。蓝草和早期民谣里,他用笔作杖,拉出一个又一个人物。亡命之徒,西部牛仔;黄沙里,煤气灯下,人为钱奔波。爱情以各种方式玩弄人于股掌之中,让人为丧失她而悲痛,为她从新鲜磨到厚茧而体会到生命的流逝。
音乐没有重量,可以随身携带,穿过相当长的时间不熄灭。鲍勃·迪伦写了很多关于音乐的哲学,重要的是,“一首歌里有什么东西,能让你感受自己的生活。”他用埃尔维斯·卡斯特洛的《加油干》解释这一条,重申“了解一个歌手的人生故事不见得能帮你理解一首歌”。特立独行的,好斗而复杂的卡斯特洛,把太多相互碰撞的观念压缩进这歌。他让人感到筋疲力尽,摸不着头脑,却也很难不在这个“我”中,看见自己的影子一闪而过。
像任何一个年长人士,鲍勃·迪伦也不吝贡献一个绝顶聪明的八十几岁老人的生活智慧(牢骚)。他认为,现在的一切都显得太“满”了。人被一勺勺喂食,所有东西都被细分营销和过度夸大。想象力衰竭,空气不能流动,梦想窒息而死。他属于没那么脆弱并且以此为傲的一代人(人类似乎一代比一代脆弱)。很会用一首歌曲伪装自己(《我一直很疯狂》——by 韦伦·詹宁斯),使人混淆发疯和精神失常之间的区别,他也看得清楚,又要说穿。
《答案在风中飘》目录
现代生活的荒谬之处在于,一方面处处把人逼疯,一方面又鼓励人们对各种刺激的耐受度越来越低。痛苦和疯狂被视作全然负面的存在,务必以各种手段将之除尽(鲍勃·迪伦把药物称作“”)。即使不能,也要用回溯童年式的心理咨询和药物把它包裹、深藏。不能让外人看出,否则小心,你会被当作社会的不稳定分子。
没错,如果你精神抱恙,人们会对你抱以同情,但内心深处总是怀着警惕。在这件事上,鲍勃·迪伦把心理医生、艺人和公众全都嘲讽了一遍。太刻薄吗?有一点他说得没错,唱这首歌的韦伦·詹尼斯也许疯了,但绝不是精神失常。
鲍勃·迪伦喜欢这些歌,它们或多或少照亮过他的心灵。在一些歌里,他似乎发现了永恒的秘密。迪恩·马丁的《蓝月亮》,许多人翻唱过的“嘟-喔普”鼻祖,由一段德彪西的旋律引出金色的月亮。“这首歌没有任何意义,但它的美含在旋律之中。”迪伦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迪恩·马丁事业巅峰期在金沙酒店的现场录音。随后笔锋一转,魅力四射的歌手,醉倒在日落大道的餐厅里。他只是这首歌一个潦倒的影子。
“这首歌穿越时间,跨越所有文化深渊。”他把最好的赞美都送给《蓝月亮》,因为它的旋律和编曲本就很好。简单的歌词使它具有普适性,人人都可以欣赏。《蓝月亮》属于每一个唱过它的人。
同样被数不清的歌手翻唱过的《无论晴雨》,被刻上朱迪·嘉兰的名字。关于这首歌,鲍勃·迪伦想讲的是真挚。真挚和单纯不同,锡盘巷的肤浅者和真正的天才不应被混为一谈。决定性的爱,存在于潜意识的深处。因为这种存在,这首歌从不虚伪,从不令人感到厌倦。
与爱相生的是痛苦。二者俱在,就会生出诗。家人悲惨死去的桑提-达科塔印第安原住民领袖约翰·特鲁德尔,即使在心碎和梦想破灭之后,也一直在写诗。鲍勃·迪伦把他比作古希腊诗人,“不是跑到水牛比尔的《狂野西部秀》上当明星的原住民”。特鲁德尔不碰那些流行的话题。尽管特鲁德尔奇迹般地活到了新世纪,《不再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歌名叫“Doesn’t Hurt Anymore”——“不再(感到)痛苦”,可痛苦仍旧坚硬地存在。
这首歌让人心碎。迪伦相信,“唯一能让我们切实团结在一起的就是苦难,而且只有苦难”。
每个人都会尝到痛失所爱的滋味(除非你有人格障碍)。每个人也都必须和钱扯上关系,倒霉一些的更会被它牢牢缠住。只有一样东西无法被钱买到,对富人穷人一视同仁,就是时间。《钱啊,宝贝》使他得到这条结论。歌手唱出来的感悟虽然平淡无奇,也没有妨碍作者就钱和时间展开论证。鲍勃·迪伦自己想必也得意,放任了记性很好的那类人需小心流露的天赋(以免招来白眼),列举了一长串跟钱有关的歌。还说,“要是每说出一首关于金钱的歌就能得到五分钱,那我可就发财了。”
这些可都是人生经验。鲍勃·迪伦不仅对钱颇有见地,多次进出婚姻的他,也对婚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留下她更划算》——by 约翰尼·泰勒,包含精英教育不能给你的生活智慧。干嘛要付给离婚律师巨额咨询费,既然知道他们是吸血虫,专门从不幸中牟利?鲍勃·迪伦有感而发,写了一堆故意激怒人的话,鼓吹多配偶婚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婚姻。又讽刺那些视婚姻的承诺如空屁,撕毁神圣契约的离婚人士。
至于歌本身,他几乎什么也没写。因为歌名就是全部——留下她更划算。他列举婚姻的种种玻璃幕墙,世俗的、法律的、宗教的、神圣的、投机的、抚育后代的、朋友式的,唯独没有爱。婚姻的契约中,爱究竟能否存在?答案在风中飘。老鲍勃告诉我们,打破玻璃天花板,去自己寻找答案吧。
答案在风中,答案在路上。“不断前进,这样更好,让火车不断前进。”比利·乔·谢弗的《流浪的吉卜赛人威利和我》是一首神秘的歌。鲍勃·迪伦认为,歌里的人物比歌名里出现的更多。他们扑面而来,倏忽而去。“你得睁开眼,要不然可就来不及了。”于是你听他的话注视着,试图看透眼前的景象。可音乐远比这要神秘。
平·克劳斯比的《威芬博夫之歌》,一首咒语溜出小圈子的歌,神秘主义的喘息进入大众的耳朵。尽管除了极少数人,无人可解这密语,这首超越中产阶级理解范围的歌,仍然能够属于每一个人。
它是如此的不容置疑,“生来注定,直接出自命运之书”。近代的科学曙光未能照耀到它。它保持古代的缄默,不管所谓命运背后的天性或者时代因素。
如果说命运太抽象,鲍勃·迪伦告诉你,同样抽象的音乐有无法解开的奥秘,就可信得多。歌词为耳朵而写,不是为眼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迪伦,歌词可以当诗来读。但他仍旧要指出,忽略歌词与音乐结合时的魔力,是批评家多么常见的错误。话题又回到艺术的想象空间。艺术无法计算,不能复制,“最好的情况是一加一等于三”。
艺术家和批评家之间的不爽永远不会消失。批评家这种职业再蠢,也不妨碍鲍勃·迪伦穿进他们的靴子。必要时,他可以像最一本正经的批评家,像写“感恩而死”的《一直舞》一样,细细拆解一首歌。
迪伦说他们“本质上是个舞曲乐队”,并就这一点展开阐述。他像一只猫,深度梳理一首歌的毛发。而后忽然撞进一扇活板门,掉进一条街。总是同一条主街,怀旧的,年轻过的,如今已不再年轻的主街。在芝加哥、纽约、底特律、新奥尔良或休斯顿,都没有差。穿越了时空的漫长烘托之后,“感恩而死”确保把这句经典歌词送进你的耳朵:“这是一次多么漫长而又奇异的旅行。”迪伦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感同身受。
“猫王”和弗兰克·西纳特拉在书中反复出现。他们是有缺陷的音乐巨灵。一位搭上时代的高速车,一头冲进沙漠里的奇迹之城,在拉斯维加斯充当放纵的活招牌。一位据说本人和音乐很不一样,但就是能够把每首歌唱成自己的。
还有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的篇章,比如迪伦写歌中人物和歌手命运的一些文章,像日本传统的剪纸画“切绘”,越看,越立体、复杂,越看之不尽。
在这些老歌里,凝固了他的青年时代。人总是对童年时代的气味和青少年时代的音乐记忆最深,鲍勃·迪伦也如此。他一张又一张地翻唱弗兰克·西纳特拉的歌,回到歌词和旋律作为歌曲的基石,而非节奏、律动和制作时期的音乐。
这是他的时代。不管今天的音乐是更好抑或更坏,我们都不能再回头。只能在读一本书和听一首歌的时候,短暂地瞥见水底游过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