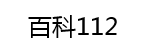斯民小学108届毕业生和老师们在孝坤楼前合影。(受访者供图/图)
“五指峥嵘太白东,上林文化孕育中。我辈同到光明地,快乐真无比……”斯民小学的校歌,我听见过两次,次是在王丽导演的纪录片里。当我在教学楼里穿梭,看各个年级的孩子早读时,其中一个教室传出了歌声,十余个孩童读书读得倦了,不知怎么就唱起了校歌。
报道告一段落后,我仍会时不时想起这个地方,尤其是那些与孩子们交流的时刻。
劳动课结束后,思琪把从菜地里刚拔的韭菜塞到我手里,鼓励我尝尝。这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告诉我,之前在江西老家的学校,虽然也有许多玩耍的空间,但老师会体罚学生,她见过同学的椅子被踢翻,“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她的成绩到了三年级就一落千丈。现在她自觉成绩“好多了”。
子清也是转学生,从杭州过来。他啃着甜筒出现在周末的校园里,身后跟着几个游客,他手里的正是当导游的犒赏。这个小孩似乎动静皆宜,很爱读书,碰面那回,他带了本《老舍文集》,平时有空,又满村子跑,古民居千柱屋里的住户,他说自己全认识。从校长斯剑光口中得知,他的父母将他转过来,是为了不让他太辛苦。
适度跨区域招生政策实施后,越来越多外地家长想让子女来斯民就读,其中一部分人是看中这里的简单与自然,接近他们童年的学习环境。
斯剑光总结的“整个村庄就是一个学校”很准确,这是乡村学校得天独厚的优势。乡间小径代替了车水马龙的公路,孩子们可以撒开腿奔跑,溪岸边放风筝,草地上捉昆虫,泥土、叶片、花朵、溪水,周边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课程里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获得的知识源于生活,也用于生活。
不仅是孩子,学校里的大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熟悉亲密的。老师吕淑斌进学校之前,从周围的李树上摘果子,装了满满一口袋。整日坐在校门口的保安,用竹子做了一桌子工艺品。正因如此,他们可以顺畅无阻地带动孩子们探索身边的世界。老师宣舒颖说:“慢慢生长才会牢固。”这些教育者看待学生们,大概真的如同园丁看着树苗。
在这里,我看到了乡土文化对人的滋养,也看见乡村基础教育的不易。“本乡本土的孩子怎样走出大山,只能靠学业成绩,这是没有办法的。外来的是来享受自然轻松教育,不希望在学业上有太大的负担。”镇中心学校校长侯科顶指出斯民面临的平衡难题。之前,斯民在学业质量调测中排名很靠后,这几年师资调整后,有了起色。
难点在于,与城镇教育并行的乡村教育,不是对前者一味借鉴便能有成效,农村的现实与资源,决定了乡村教育在升学以外,还有许多亟待达成的目标。
在走访村子时,我听王丽谈起一个初二男孩,因为家庭关系变动患上了抑郁症,他身边几乎没有能够听他说话的人,回到家,强势的奶奶只会以念叨他好好学习的方式,来表达关心。他的天资很高,在斯民上学时,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现在却几乎无法继续学习。
这种情况在留守家庭里大概不罕见。许多孩子的父母外出打工,忙于生计,无暇照顾他们,孩子在精神层面也普遍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指引,仍有一部分农村学生今后会辍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应当在小学阶段的教学设计里,把对学生的生活的关注,放到与书本知识学习同等的地位上?长期以来,我国的课程内容一直是城市本位的,对于农村孩子而言,课堂上的知识都是一些陌生的事物与体验,如何充分挖掘与利用好农村乡土资源,成为学校独特的教育资源?
从斯民小学的发展中,可以看见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王丽八年前到访这所村小时,它除了书法教育,还没有建立起太多的特色。眼下,校长和老师更有意识地把传统与自然之美带到孩子的生命里,并以一种亦师亦友亦亲人的关系陪伴他们。
在校园里嬉戏、学习、劳作的孩子们,看上去大都很舒展。有一个被称为“老油条”的女孩,性情桀骜,像只刺猬,李一斌观察到,相比两年前,她现在的眼神变得柔软了。这便是一个宽容的环境能给人的礼物吧。
参观华国公别墅那天,斯剑光站在田垄上说:“在快节奏的城市里面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感,农村里面哪怕什么都没有,他还是觉得我在这里是有根的。”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外地家长特地带孩子从城市来到这里念书,也是一种回归。反观许多农村孩子,自幼接受的教育是对城市与工业的歌颂与向往,对自己生长之地,缺乏深入体会和留恋。经济上的匮乏可能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自卑,精神上也在流浪,无所依归。乡村教育,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他们获得身份认同与自尊?
不同于许多千篇一律的学校,斯民小学因其历史,更因其人而具有一种锚点的意味,这让我相信在毕业典礼上唱着《西风的话》落泪的孩子们,未来忆起在这里度过的光阴,一定是清晰可感的。祝福他们。
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