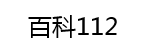伊莎贝尔为芬妮做的事可比单单告诉她振作起来多得多。芬妮之前从她父亲老艾力克·米纳弗那儿继承的所有财产,都投资到威尔伯的生意中去了。然而,随着威尔伯身体日渐孱弱,他的生意也衰败了,在他去世前就彻底垮台了。如乔治·安伯森所说,他和芬妮都被“一个精确的奇迹毁掉了身家”。他们“没有一分钱,也没欠一分钱”,他解释道:“就像淹死前的那一瞬:你不是在水下可又爬不出来。你所知道的只是你还没有死而已。”
他的话很有哲学意味,并且有从他父亲那儿继承的“远见”可依靠,但芬妮既没有“远见”,也没有什么哲人的头脑。幸运的是,有一份关于威尔伯财产的法律文书表明,威尔伯的人身保险没有被殃及。伊莎贝尔非常赞同儿子的想法,于是立即将这笔资金转到了小姑子的名下。若是用于投资的话,获利会比每年900美元还要多,如此芬妮就不会变为穷光蛋或寄生虫,但这点还有待考证。乔治·安伯森努力给芬妮打气,“虽然说情况险恶,但不管怎么说你都是继承人。”她笑不出来,安伯森继续幽默地打趣道:“芬妮,想想900美元是多么可观的收入啊:跟你同一层次的单身汉,一年得挣够49000美元才行。然后,瞧,为了年收入能达到50000美元,你唯一需要做的是,当那单身汉穿着行头来向你示好的时候,给他一点点鼓励!”
她无力地看着他,凄凉地低声说道还有“针线活要做”,接着就离开了房间。安伯森冲着伊莎贝尔感概地摇了摇头。“我常常觉得幽默不是我的长项,”他叹了口气。“上帝啊!她根本没怎么‘振作’起来!”
假期到了,乔治·安伯森·米纳弗没有回家。伊莎贝尔去看了他,二人一同去南方待了两个礼拜。在落脚的酒店里,伊莎贝尔为自己有这么个健壮英俊的儿子感到骄傲。当她看见人们在客厅里或是宽敞的阳台上盯着乔治看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享用美酒佳肴——的确,她是如此为儿子自豪,以至于全然没有意识人们其实是在饶有兴趣地看她。比起乔治不可一世的模样,他们更有兴致欣赏她的美丽,并且充满友好和赞赏。能有两周的时间与儿子在一起,伊莎贝尔非常开心,她喜欢和儿子散步,靠在他胳膊上,和他一起读书,一起看海——但最喜欢的可能还是和他一起走进宽敞的餐厅的时刻。
然而,两人还是不时感受到了这个圣诞节和以往的不同——毕竟,这是个悲伤的节日。但到了六月份,伊莎贝尔参加乔治毕业典礼的时候带上了露西——事情似乎开始不同了,特别是在毕业纪念日那天,乔治·安伯森和露西的父亲也来了。尤金之前在纽约出差,安伯森轻易地说服了他一同前来,五人玩得很愉快,毫无疑问,这位新毕业生成为了英雄和焦点。
舅舅乔治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在这儿上学时就住在那边。”他说道,指着学校里的一栋建筑给尤金看。“不知道乔治是否愿意让我的那些崇拜者们在那儿立块牌匾纪念一下。要知道,他现在管着这儿的一切。”
“你在这儿的时候不也是这样么?有其舅必有其甥。”
“别告诉乔治你觉得他像我。在这个时刻,我们得留心这位年轻绅士的感受。”
“是的,”尤金说道。“否则的话,他会让我们都消失的。”
“我确定我像他这么大时不至于这样,”走在拥挤的参加毕业典礼的人群中,安伯森斟酌道。“一则,我有兄弟姐妹,母亲不像乔治的母亲那样溺爱孩子;二则,我也不是唯一的孙辈。我父亲对乔治可比对我们这一辈溺爱得多了。”
尤金笑了起来。“你只需用三条就能解释小乔治的优劣势了。”
“三条?”
“他是伊莎贝尔唯一的孩子。他是安伯森家族的人。他是个男孩。”
“好吧,犀利先生,这三条中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劣势?”
“它们同为优势也同为劣势,”尤金说道。
说到这儿,他们恰好看见了谈话中的主角。乔治正和露西在榆林中散步,手中的手杖点来点去,向露西指出在过去的四年里,对他而言有各种历史意义的事物和地点。舅舅和尤金评价说他的姿势很是随意优雅,发现他的态度中流露出不自知的高贵气息,俾睨拥有着脚下和周围的土地、头上的树枝、前方古老的建筑,还有露西。
“我不明白,”尤金说道,笑得很古怪。“我不明白。谈及他作为人的人性问题时——我搞不懂。也许他更像是神一样的存在。”
“我那会儿不是这样吧!”安伯森呻吟道,“不会每个安伯森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吧,你觉得呢?”
“别担心!这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因为年轻貌美并拥有大学教育背景。就连最高贵的安伯森家族的人都内化了他们的贵族气,变得平易近人起来。只是,这不光是时间的问题。”
“我想的确不止是时间的问题!”乔治舅舅赞同道,懊恼地摇着头。
接着他们走到那位最可爱的安伯森——伊莎贝尔身旁。在她身上,似乎没有任何时光的痕迹,也从来都没有烦恼。她正独自站在大树下沉思着,远远地陪伴着乔治和露西。不过看见两人走来,她就迎了上去。
“真好,不是吗!”她说道,戴着黑手套的手指向漫步在周围,套着夏装的人们,还有簇拥着各自主角的人群。“他们看起来那么热切,那么自信,所有这些男孩子们——真是感人。当然,年轻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
安伯森咳嗽了一声。“不,严格来说,年轻人似乎并不会认为青春易老!我和尤金刚刚谈到了这点。你知道每当我看到这些欢欣鼓舞,年轻光滑的脸庞时,会想到什么吗?我总是在想:‘哎,你得使劲抓住青春!”
“乔治!”
“哎,是的,”他说,“生命真是神奇啊:给每个母亲的儿子都准备了特别的打击。
“也许,”伊莎贝尔不安地说道——“也许有些母亲可以代替孩子承受这些。”
“没人能做到的!”她哥哥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没有任何一个母亲可以让长在儿子脸上的皱纹长在自己脸上。我想,你是知道所有这些年轻的脸庞都会长皱纹的吧?”
“也许他们不会的,”她憧憬的微笑着,“也许时代变化了,没人非得长皱纹了。”
“据我所知,这种事情只在我认识的一个人身上发生过,”尤金说道。看着伊莎贝尔问询的眼神,他笑起来,她才明白自己就是那“一个人”。而且,他倒是没说错,她很清楚这一点,双颊浮现出迷人的红晕。
“是什么让脸上长皱纹的呢?”乔治·安伯森问道。“是岁月还是烦恼?当然,不能说是智慧让皱纹生长——不能对伊莎贝尔无礼啊。”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让皱纹生长,”尤金说道。“年纪是原因之一,烦恼也是,还有工作。但是,缺乏信仰是刻下那道最深皱纹的原因。平坦祥和的额头代表着最充实的信仰。
“对什么的信念呢?”伊莎贝尔轻声问道。
“对所有的一切!”
她不解地看着他,尤金又笑起来,就像刚才她这么看着他的时候一样。“哦,是的,你就是这样!”他说道。
她疑惑地盯着他,目光里有种不自知的渴望,还透露着笃信,仿佛打心底里相信尤金说什么都是对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若有所思地垂下眼睛,埋头不语。突然,她抬起了头。“哎呀,我相信,”她惊喜地说道,“我相信我就是这样!”
安伯森和尤金都笑起来。“伊莎贝尔!”哥哥乔治叫道。“你这个傻瓜。很多时候你看上去也就十四岁!”
这句话让她蓦然想起了此刻的使命。“天啊!”她说道。“孩子们去哪儿了?我们必须赶快找到露西,乔治得去和同学们坐一起。我们得赶上他们。”
伊莎贝尔挽起哥哥的胳膊,三人向前走去,在人群中寻找着孩子们。
“奇怪,”安伯森说道,他们没能立刻发现两个年轻人的身影。“还以为就算在这样一个大场合下,也能一眼找到俾睨一切的‘主人’呢。”
“今天可是有成百上千个‘主人’,”尤金提醒他。
“不,他们只是这学校的‘主人’”,乔治舅舅说道,“我们找的是全宇宙的‘主人’。
“他在那儿!”伊莎贝尔开心地叫道,一点都没在意哥哥话中的讥讽。“他看起来不就像宇宙的主人吗!”
当他们与全宇宙的“主人“还有他漂亮的朋友会合后,尤金和安伯森仍在取笑伊莎贝尔。虽然两人不肯说出发笑的缘由,露西一再要求也没用,可这开了个好头,一整天五个人都非常愉快——具体而言,其中四人高兴的为第五个人捧场,而第五个人也很是亲切和开心。
在班级里,乔治在学业和社交方面都不出众。看起来他对这两方面的活动一直都保持着有节制的嘲笑,他自己的“圈子”“很少参与这两方面的事情,”他跟露西解释道。也没说清他的圈子到底做什么了。除了的确参加了一些音乐喜剧之外,隐约间大概他们什么都没干。在回应露西的提问时,乔治有个反问显然证实了这一点。“难道你不认为,”他说道,“真的,你不认为是什么比做什么要好得多吗?”
他说“好得多”的时候,口齿含糊不清,似乎故意这么做的,完全是有心的。后来,露西向乔治模仿他的语调,可乔治并没有笑:他自己也多多少少会这样讲话,这也是他四年里所学之一。
他还学到了些什么?若是有人这么问,并给一定的时间让他直接作答,那他可能会不知道该如何去讲。他学会了怎么“临时抱佛脚”来通过考试:也就是在三四天内,往脑子里填进够用的学科片段,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还有语言的,能够让他在10个试卷上的问题中头头是道地答出6个。他的本事就是短期记忆这些信息,正好够拿到一个好分数,之后这些记忆就消失殆尽,不留一丝痕迹了。就像他的“圈子”一样,乔治不仅喜欢“是什么”胜过“做什么”,而且非常满意自己在四年里为“是什么”而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今后继续“是什么”做准备。当露西十分羞涩地追问她朋友口中那高贵美好的“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乔治·安伯森·米纳弗轻轻扬起了眉毛,意思是这不需要解释她也该懂得,不过他还是做了解释:“哦,我想是继承家族之类——成为一位绅士。”
露西朝地平线方向看了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