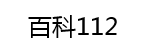2023年5月18日至19日,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图为峰会会场大唐芙蓉园。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23年7月9日,满载货物的X8008次中欧班列驶入西安国际港站,标志着中欧班列境内外全程时刻表班列首次实现了有来有往,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丝路沿线贸易互通注入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总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本网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进行解读。
主持人:王学斌 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主任
嘉宾:孔德立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
邵声 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家国同构特性构筑了命运共同体,天下一家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王学斌:在总所总结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中,“和平性”殿于最后,此种安排自有其深意。一方面,正因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和包容性,方能在久久积累下形塑牢不可破的和平性理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具备独特自然禀赋和气候条件的超大型文明,中华民族对空间的渴望、对资源的获取,我们有着自己的一套宗旨。
孔德立: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由中华民族独特的农耕文化决定的。古代不同区域的人们由于生存的地理环境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钱穆先生总结为三种文化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追求和平,就成为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与心理诉求。
纵观中国历史的演进,作为人类生活主流的生产方式还是农耕,因此,农耕文化积淀的和平性正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特性。根植于农耕文化的和平理想为人类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由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传统决定的。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首篇《尧典》提到“协和万邦”,为政者以“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的理念,秉持“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原则,致力于“协和万邦”。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奠定了后世德治与礼治的治理模式,不断指引着中国在和平道路上发展前行。西周建立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制度,依照大宗小宗的亲疏远近,辨别政治贵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的贵族,除了少数异姓贵族,大多数都是姬姓贵族。即使是异姓贵族,诸侯以下的贵族也是与诸侯同姓的。总体上说,周代的封建制度是政治制度,也是家族制度。这种家国同构的独特性就构筑了周代的家国命运共同体。天下一家的理念,从此深深印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
司马迁的历史观受孔子影响很大。孔子根据鲁国历史修《春秋》,实则是为后来的政治秩序奠定了礼治的基础。董仲舒认为汉代治国应以《春秋》为标准,以“《春秋》决狱”。“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正是礼治的写照。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三千弟子,其内涵是传承饱含文德的历史文化传统。从《尚书》到《春秋》,再到《史记》,无不传承着和平与厚德的历史传统。中国汗牛充栋的历史典籍,无论是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还是地方志、家谱等家国天下史书,都始终贯彻着和平主义的理想与书写传统。
邵声:中华文明是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文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孕育出爱好和平的情感信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学说。比如,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道家推崇道法自然、无为无争;墨家强调兼爱相利、非攻尚同;甚至连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谋、非危不战。在之后的数千年里,中国的和平观进一步吸纳、发展,并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途径渗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刻入到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和平”也由此上升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一,塑造出中华文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正是基于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带给世界的始终是和平与交流,而非战争与殖民。即使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的和平信念也从未消退。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华文明的这种和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其他人类文明的感知与赞扬。例如,公元5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摩西在其《亚美尼亚史记》中表示,中国人“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英国哲人罗素认为:“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
中国哲学中的仁爱和平理念贯通心性与天道自然,使得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和平发展
王学斌:中华文明珍爱和平,五千年来,绝少有我们主动发动的军事征伐事件;中华文明倡导和睦,五千年间,中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之佳话绵延不断,代代相传;中华文明主张和谐,五千年中,无论是中华民族的内心世界的构建,抑或国与国间的相处,皆是以德为尊,以和为贵,一种将道德秩序置于首位的思想体系油然而生,且根深蒂固。
孔德立: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是中华民族的仁爱思想浸润的。基于农耕文化重视天人合一,维护群己关系的特性,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孔子创造性地把“仁”“礼”结合,从而给“礼”种下“仁”的种子。仁不是利己,而是利他。在处理群己关系时,仁爱不是爱自己。《论语》中的“人”是指他人,不是指“我”。《论语》中的“我”,是“己”。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春秋繁露·仁义法》)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可见,仁是成就他人。
孔子努力培养弟子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孟子在战国兼并战争时代,努力劝说国君以恻隐之心行仁政。如果说,孔子是在培养担任礼治重任的君子,孟子则是以仁政方案努力说服国君,不要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应回归政治最本初的意义,关爱百姓,保护民生。
战国时代,诸侯之间兵戎相见,百姓看不到和平的曙光。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仁爱与和平,是孟子追求的理想政治。
从“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从“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皆体现了人性的光辉。仁爱浸润的中国哲学,具有独特的和平理念。
孔子的“泛爱众”,经过孟子的阐释,成为仁义礼智之四德。张载“民胞物与”的理念,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进一步把中国哲学中的仁爱和平理念贯通心性与天道自然,使得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和平发展。
中华文明爱好和平具备仁爱特征,并不是任人宰割、忍气吞声的羔羊。爱好和平,和而不同,并不代表因“和”而放弃自己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应有“礼”来节之,就如同爱需要分辨是非。
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赞同“汤武革命”,都是以仁爱求和平,以牺牲自我保存民族大义的可贵精神。自强不息、敢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是维护和平的不竭动力。
邵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本根、坚持“两个结合”,更加自觉地从历史、文化、文明的维度深化对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建构中国的和平话语,提出“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并通过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使中国的和平主张与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也得到进一步光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王学斌: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华民族无论过去、今天还是未来,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也是我们能够在新时代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主张的文明属性使然。
孔德立:总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这一论断揭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吾国吾民族的“生命”。如钱穆先生所言“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了文化,那就等于没有了生命。因此凡所谓文化,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延精神”。绵延至今的文化积淀着的和平属性,是中华民族的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始终以和平性为底色。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并日益迸发出无限生机的根本特性。中华文明的和平底色,为人类文明发展持续贡献智慧与力量。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既是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又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做出的科学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为深刻阐释“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新的力量支点。
邵声: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既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想,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和平相处与自由发展的理想,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结合”追求中国与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2014年,总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一观点不仅突显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还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双重和平基因已有机结合并融入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更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由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决定的。2015年,总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并把和平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素,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于和平的深厚情感与执着信念,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
与此同时,总还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理念,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动力所在,“新型国际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优先、均势制衡、零和博弈、国强必霸、文明冲突等逻辑,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与方向,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这些新的和平主张与实践,不仅再次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也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